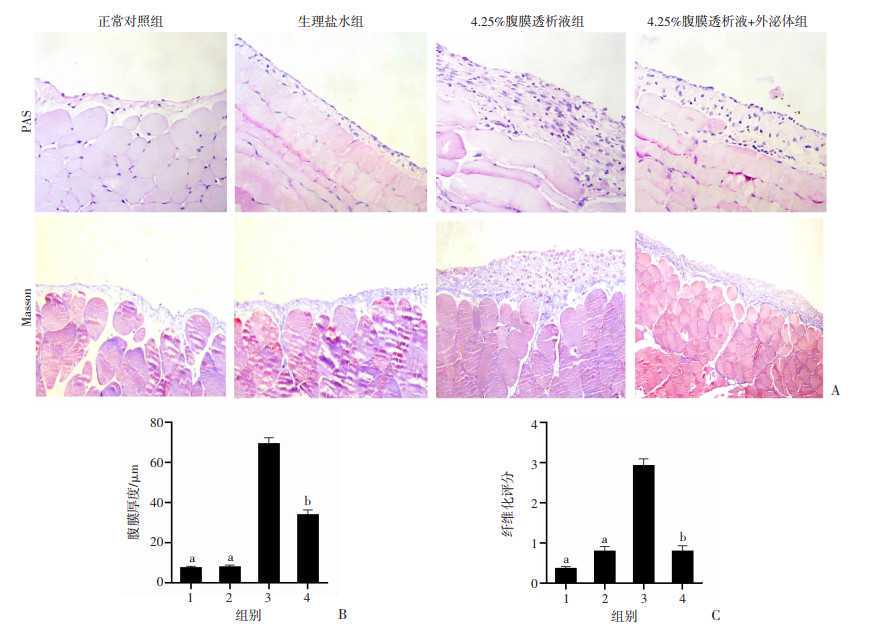首发网哲邻人部,屋顶授权转载
第七章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序言[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妇女运动见证了女性主义运动和学术在新一代青年女性主义者中复苏,因其发生之突然、规模之大,故有人将其称为“性别地震”(Wolf,[1993)1994:25)。在1992年,这些女性激进主义者成立了“第三次浪潮直接行动[ThirdWaveDirectAction]”——一个旨在政治上动员年轻人和培养年轻女性领导力的组织。到1996年,ta们已经成立了“第三次浪潮基金会”——一个致力于支持15到39岁妇女参与到面向性别、种族、社会和经济正义之活动的全国性机构。
第三次浪潮激进主义的激增,部分是对那些在1982年就声称女性主义已死或不再有意义的媒体的回应,当时的杂志将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女性称为“后女性主义者”一代(Bolocin,1982)[2]。当丽贝卡·沃克(RebeccaWalker)在杂志《女士(Ms.)》上宣称:“我不是后女性主义者,我是第三次浪潮。”(1992:41,heremphasis),这是对那些为女性主义哭丧者/高高在上宣布女性主义的讣告者之蔑视(Henry,2004)。尽管“第三次浪潮”成为了这些年轻女性认同她们新形态女性主义的旗帜,但要清晰地辨认她们并非毫无难度。关于她们,更多所提及的是年龄,而不是她们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激进主义的贡献。一些作家用出生年龄去区分她们,如于1963年和1974年之间出生的可以被称为第三波,然而其他人则是用更为共通的形象去描述,“X世代”、“某些意义的二十岁”、“简[Jane]世代”就是这些共通形象的产物(HeywoodandDrake,1997;Kamen,1991;Johnson,2002)。“母-女”也被用于去形容这些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同她们的上一代,也就是第二波前辈的关系,因为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冲突或叛逆/反抗早已是母女关系之间的常见主题。
本章着重于作为理论观点的美国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即,任何女性主义者,不论高矮胖瘦、年轻与否、阶级出身,都将被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所拥抱。尽管在美国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中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观点,但ta们的主要出版作品中都有一些必须被重视的理论假设,正是这些理论假设才使得我们能够讨论她们对女性主义思潮的独特贡献。同时,我们将研究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是从后结构主义和交叉性理论之中被作为一个综合体所建构出来的(Siegel,1997;Mann,2013)。称其为人造衍生物(syntheticderivation)并不是说第三波议程缺乏独创性,相反,正是因为第三波以复杂的方式交织着这些早期女性主义的各个特征,使其变得新颖、可研究。
第三次浪潮的历史基础
当第三次浪潮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步入成年时,她们遭遇的世界与第二次浪潮的前辈们已截然不同。政治上,她们面临“新右派”(NewRight)领导下高度动员的保守主义反击,这个派系在里根/小布什时期的政坛影响甚巨。新右派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里根总统选举和STOP-ERA运动使福音派基督徒和更世俗的保守党人联合起来的结果。相比之下,第二次浪潮则是在强劲、自由、左翼的社会运动中兴起的,诸如民权运动和反越战。
经济上,第三波女性主义者面对的是二战以来最差的就业市场,也是战后第一代预期会混得比父母一辈差的人(HeywoodandDrake,1997)。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衰落,以及低薪服务业工作的增加,第三波女性主义者MichelleSidler将这个灰暗的经济时期称作“活在麦当劳”(Sidler,1997:25)。她讨论了大学学费的高价如何让她的同辈人背负巨债,即使幸获学位,高薪工作也少之又少。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段经济衰退和社会向下流动的时期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生活的战后经济繁荣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次浪潮也成长于新电子和数字技术兴起所酝酿的“新信息社会”和全球“技术文化”(HeywoodandDrake,2004:20)。第三次浪潮者的生活浸渗在崇尚消费主义和广告的大众文化之中,发声以新闻的形式传播。因此,新的浪潮把大众文化作为其主要抗争阵地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好的一面来说,新技术为第三次浪潮创造了传播思想和参与在线组织的新方式,这是前人未有的选项(AlfonsoandTrigillo,1997;Duncan,2005)。
在性别议题上,第三次浪潮的道路部分是由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先前取得的成果铺就的。虽然第三次浪潮被指责花太多精力批评她们的女性主义前辈,而非女性主义的外部敌人(Henry,2004:82),但许多第三次浪潮者都向这些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致敬。选文93来自JenniferBaumgardner和AmyRichards的《第三次浪潮宣言》(2000),即是对第二次浪潮成就的致敬,它提醒我们在第二次浪潮成功之前的1970年,对女性来说美国是什么样的。
第三次浪潮与交叉性理论之间的暧昧关系
许多第三次浪潮作者,无论其种族或民族背景如何,都将自己的系谱追溯到第二次浪潮的有色人种妇女、她们开创了交叉性理论。例如,在《第三波议程》(1997)中,编辑莱斯利·海伍德(LeslieHeywood)和珍妮弗·德雷克(JenniferDrake)说:“是美国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塑造了一种语言和原则,可以解释我们在世纪之交的生活”(1997,13)。《不是我母亲的姐妹》(NotMyMother'sSister)一书的作者阿斯瑞德·亨利将“对在多种压迫中同时存在、相互交缠的本质的洞悉”看作“第三波女性在学习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不得不品尝的一道美味教训”(2004,32)。
选自黛西·埃尔南德斯(DaisyHernández)和布莎拉·雷曼(BushraRehman)共同编辑的论文合集《殖民地这![ColonizeThis!]今日的女性主义有色妇女》(2002)的选文95将这本文集形容为第二波交叉性理论者首次发起的“再次对话”(2002,xxi)。

在多数的第三次浪潮主要出版物中都可以发现对多元性的不对等承诺和被压制的知识(指被主流群体忽视、沉默或认为不太可信的共同知识)的检索。第三次浪潮文集的编辑者们如履薄冰地将多元的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的作者纳入其中。在《殖民地这!》(ColonizeThis!)(2002)后,如《现实一种》(ToBeReal)(,1995),《听好了》(ListenUp)(Findlen,1995),和《不同波长》(DifferentWavelengtbs)(Reger,2005)等选集都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差异的典范。许多第三次浪潮作者都在对妇女之间的差异有敏锐认识的同时,对本质主义持批评态度。
其所表达的是,与其把激进主义分子带入妇女运动中来,不如将女性主义带入到激进主义分子里去(Mack-Caney,2005;Dicker,2008)。
与交叉性理论家一样,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作者也呼吁对那些学术界内外的多种理论生产场所、以及常被习惯性地称为理论的活动进行更加广泛的描述。她们与交叉性理论家尤其相同,都对社会生活中的知识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一点可以在她们表达观点时对自己身上的小叙事运用自如中看到。第三次浪潮文本的分析者表明:“大多数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迅速将自己定义为非学术性的。”(GillisandMunford,2004:168)。例如,第三波女性主义作者维罗妮卡·钱伯斯(VeronicaChambers)和琼·摩根(JoanMorgan)就强调了她们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社会生活知识与她们在妇女研究课上获得的学术知识之间的区别(Chambers,1995;,1999)。两人都对"学院女性主义"——如何经常被视为唯一被授权戴上大写字母"F"的女性主义桂冠——这一知识形式提出批评(Henry,2004:172)。琼·摩根在她的经典嘻哈作品《庭院里有两只鸡》(1999)里,呼吁建立一种与嘻哈相似的、能与年轻黑人妇女对话的女性主义。她担心,“如果女性主义要与绝大多数黑人妇女联系起来……那她就必须把自己从学院的象牙塔里拯救出来”(,1999:76)。摩根还分析了弥漫在嘻哈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矛盾,并解释她是如何处理对嘻哈的热爱和嘻哈中所含有的厌女情绪的这种矛盾。
这种对流行文化进行的政治性介入在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尤为明显和普遍。许多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被暴女这种音乐风格所启发,于是通过制作自己的音乐、杂志,发展自己的唱片公司等手段,在朋克摇滚的世界中为女性创造了自身的空间与安全(Klein,1997)。暴女们所采用的自力更生原则被许多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们所接受,她们经常描述自己通过制作杂志和创建赛博讨论组来传播ta们的政治信息所体验到的赋权(BaresandMcHugh,2005;Duncan,2005)。选文90是一张约在1991年的名为《比基尼杀戮》杂志的封面,现在可以在《暴女全收集(TheRiotGrrrlCollection)》(Darms,2013:122)中找到。比基尼杀戮是一个朋克乐队,由KathleenHanna、BillyKarren、KathiWilcox和TobiVail组成,被认为是暴女运动的先驱。这样的杂志说明了这样多种形式的理论化所能释放出的创造力。
第三次浪潮与后结构主义及酷儿理论之关系溯源
第三波也追随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的脚步,拒绝身份政治。丽贝卡·沃克写道:"我们担心身份会支配和规制我们的生活,瞬间将我们与某人对立起来,迫使我们选择固着不变的一个立场,女性与男性对立,黑人与白人对立,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对立,好人与坏人对立(1995:xxxiii)。同样地,DanzySenna认为,"挣脱身份政治的束缚"使她"认识到我们所继承的世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Senna,1995:20)。第三次浪潮渴望更多流变的身份观念,这被深情地描述为第三次浪潮的"生机勃勃的混乱"(HeywoodandDrake,1997:8)。
第三波作者同样将福柯的警告铭记于心,即理论——即使是解放性的理论——往往对其支配性的倾向视而不见(Raroazanoglu,1993)。这些想法为批判女性主义自身的第三波作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许多第三波的出版物中还能看到,有些观点认为女性主义(尤其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是一种限制个人自由的规训\纪律性话语,会对妇女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权威性的评判(Henry,2004:39)。
BarbaraFindlen,《听好了》的编辑,描述了她的同行们是如何认为"如果某件事情吸引人、有趣的或流行的,它就不可能是女性主义"(1995:xiv)。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是她们的土气、朴素和太过"严肃的姐妹"的老生常谈,在其他第三波作家中有广泛的共鸣(BaumgardnerandRichards,2000:161)。与之相对地,在许多第三波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交织着对幽默与矛盾的灵活使用,正如来自苏珊·简·吉尔曼的《再见,芭比》(1998)的选文92所展现的那样。
来自丽贝卡·沃克的《真实》(1995:xxix)的选文91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归训\纪律性进行了更为严肃和严厉的描述。
在《真实》的"后记"中第二波的交叉性理论家AngelaDavis称自己惊讶地发现,Walker的文集中竟有如此多的作者感到女性主义"监禁了她们的个性——她们的欲望、目标和性实践"(,1995:281)。[4]
这种监禁的意象令我们想到福柯的全景式监狱和引导人们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其符合规范的全景式凝视(福柯,[1975]1979:155)。GinaDene的文章"MissionaryPosition"(1995年)(也在RebeccaWalker的文集中)警告我们,女性主义"规定它的边界",规定适当的女权行动,就像传教士规定适当的性行为一样(Dent,1995:71)。简而言之,对许多第三波的女性主义者而已,第二波女性主义显得过于苦行和纪律严明了。
关于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深入讨论可见于摘自《解开母/女的包袱》的选文94,CathrynBailey运用福柯的意象写作的“重评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紧张关系”(2002)。
许多年轻女性认为自己在为拒绝成为某种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女性主义者而抗争。因此,她们或许呈现了一种抵抗,这种抵抗并非直接指向现实的女性主义者,而是指向一个内在于女性主义者的治理者——"全景式的女权警察“(Bailey,2002:150)
贝利举例说明了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女性主义者间沟通的不充分,并为减少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建议。
贝利同样反对许多第三波作家所信奉的后现代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她以唐娜·明科维茨(DonnaMinkowitz)对丽贝卡·沃克的文集《真实》(1995)的贡献为例,明科维茨描述了她如何对用棒球棒雷普青少年(这一幻想场景)感到色情[erotic]、以及她如何希望能够自由地表达出这种感觉。丽贝卡·沃克称赞她所有的作者都很"真实",对所谓的"反革命行为"——那些会被大多数第二波作者所批评的行为——进行了"勇敢的反思"(,1995:)[5]。而且为的文集写了前言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GloriaSteinem,也的确对明科维茨的叙述提出了批评。贝利也对明科维茨关于自由或真实自我的相对主义概念感到不舒服。她认为,一个人仅仅认为她或他的行为是颠覆性的或有利于自由和抵抗是不够的,"在主体自己的解释和他人的解释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Bailey,2002:149)。在这里,贝利认真地梳理了困扰许多第三波著作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的问题。
《捕捉浪潮》(2003)的作者罗里·迪克和艾莉森·皮普梅尔也谈到了困扰第三次浪潮写作的相对主义问题。在其看来,女性主义含义的边界的缺席,"掏空了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纲领",导致了"女性主义的门户大开",任何观点和行为的人都能成为女性主义者(Dicker和Piepmeier,2003:17)。对其来说,这是对交叉性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格言"女性主义为所有人服务"(17)的"最糟糕解读"。尽管这些批评家已经指出第三波与后结构主义和交叉性理论的"不愉快婚姻"所产生的问题(Mann,2013:1),下面我们仍将讨论第三波与这些不同理论观点最成功的融合之一。
第三次浪潮理论的应用
选文96提供了朱莉·贝蒂(JulieBettie)的《无阶级的女人:女孩、种族和身份认同》(2003)的摘录,其中交织了交叉性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代作品之一[6]。她的书基于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盎格鲁女孩在高中生活的族群志研究。她使用交叉分析来考察种族、性别和阶级是如何在这些年轻女孩的生活中环环相扣、相互构成,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她还大量借鉴了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将社会阶级视为表演(的一环)。正如贝蒂所指出的,在她的书出版之前,这种类型的阶级分析在女性主义论著中只作为“客串”出现(贝蒂,2003:51)。
不同的班级表现\表演在她所研究的高中的不同学生群体中是显而易见的。贝蒂在此强调了理解社会阶级的文化维度的重要性——阶级差异如何反映在消费习惯和亚文化风格中——比如发型、服装,甚至女孩们涂的口红的颜色。这种差异通常被视为性道德的标志,因此工人阶级的墨西哥裔女孩被老师和其他学生视为性最放浪[active]的女孩,却不管事实是否如此。阶级差异在学生的学习习惯、课堂行为和课外活动中更加明显。简而言之,贝蒂揭露了阶级斗争\冲突[warfare]是如何在校园圈层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的。
当墨西哥裔美国女孩表现得像“保送生[preps]”时,她们会被墨西哥裔的同龄人指责为“表现得像白人”(伯蒂,2003:83-86)。一些理论称之为除籍[dismissal]策略——一种用来控制和排斥被发现具有威胁性的群体成员行为的策略(见第10章)。尽管贝蒂认识到这一点,但她也强调了这种指控是如何混淆种族和阶级类别的。例如,贝蒂问为什么表现得像白人是与阶级特权式的保送生相联系,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吸烟者[smokers]”(既然这两个圈层大部分都是白人)。解释是,墨西哥裔学生认为吸烟者无关紧要而不予理会。对贝蒂来说,工人阶级白人对这些学生的相对不可视或不重要,正是因为保送特权在学校造成了最多的阶级伤害(2003:84)。在这里,她指的不是身体伤害,而是一些理论所说的社会阶级的隐藏伤害——当人们因为其较低的阶级地位而感到不适切或不满足时、对人们自尊的伤害(SennettandCobb,1972)。
像其他第三次浪潮的作家一样,贝蒂乐于从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方法中汲取灵感。贝蒂不认为这些观点相互是矛盾的,而是自由地运用不同理论的优点。总的来说,她的作品展示了从这种理论综合中可以获得的丰富性。
同床异梦的姐妹情谊?
亨利指出了个人主义思想反映在第三次浪潮写作对微观个人叙事的偏好中。与日记或日志一样,这些个人叙事突出了她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矛盾、不确定性和困境。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则很少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写作。相反,ta们认为分析应该从个人的、个体的反应转向集体的、大众政治的反应。一些第二次浪潮的作者对第三次浪潮的写作风格进行了针对性的批评。一位批评家提到了《听好了!》一书的作者们(《下一代女性主义者的声音》(1995))是"业余的回忆录作家"、其把"感觉不好"和压迫混为一谈,"认为她们的日常生活对陌生人来说是有着更加内在的意义"(Kaminer引自Siegel,1997:67)。
亨利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们并不那么苛刻。相反,她承认,第三次浪潮的个人主义写作方法反映了她们对滥用本质主义、以及第二次浪潮的集体化的"我们"和替其他妇女说话的抵制(Henry,2005:43)。显然,这是她们从后结构主义和交叉性理论中学到的一种受欢迎的批判姿态。然而,她认为现在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超越个人性的叙述,去参与到更宏大的政治和理论探索,并从个人转向集体的时候了。
亨利对女性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定义特别挑剔,比如她引用的《新女孩文化的胸怀指南[TheBustGuidetotheNewGirlOrder]》(1999)共同编辑马塞尔-卡普(MarcelleKarp)的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DIY女性主义的时代——姐妹、要自己动手!——我们为自己起了各种名字:口红女同性恋者、自己动手的女性主义者。不管什么名字,我们仍然是女性主义者。你的女性主义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Karp引自KarpandStoller,1999:310-311)。虽然亨利赞赏像卡普这样的第三次浪潮作者的做法使得女性主义吸引了更多的男男女女,但她认为,当女性主义被表现为对个人而言想要的任何东西时,它就"失去了关键的政治视角",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车尾贴纸,对后面的司机们宣布着'女孩的权力'"。(Henry,2005:84)。
亨利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概念未免太过迎合二十一世纪美国政治的保守化现实,即强调个体对社会集体问题的解决(2005:84)。她感叹失去了共同的斗争、可定义的政治目标和有针对性的敌人(2005:91),她的结论是,通过建立共同的政治目标,第三波可以从仅仅是"一种由个人采取的单一的世代立场,转变为批判性的政治观点,在承认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差异的同时,强调需要集体行动来影响社会"(2005:93-94)。
结论
注释
1.本章的部分内容首次出现在的文章中,"ThirdWaveFeminism'sUnhappyMarriageofPoststrucntralismandlntersectionalityTheory,JournalofFeministScholarship,(May,2013)。感谢JournalofFeministScholarship和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文学院(CollegeofLiberalArtsatthe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Dartmouth)的印刷许可。
2.甚至连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新闻最后的堡垒的《》也在其周刊的封面故事中唱起了悲歌,开头是"妇女运动已经结束了"(引自Faludi,1991:76)。
3.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还提到,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在被安妮卡·希尔指控性骚扰之后、仍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确认听证会成为了点燃她们燎原般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的星星之火。正如AstridHenry所写的,"托马斯的听证会有助于使暗淡无光、被边缘化的妇女问题在反女性化的1980年代后重新进入媒体的视野"(2004:161)。
4.Davis认为,第三次浪潮者将女性主义描绘成苦行的、纪律\规训性的,但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主义状况”(,1995:281)。
5.弥漫在Walker书中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她的陈述中最为明确:"如果女性主义要继续保持激进和活力,就必须避免以极端的偏见去重构世界,无论女/男,善/恶"(,1995:xxxv)。
6.Bettie的书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美国社会学协会性(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Sex)与性别分会(GerSection)2004年最负盛名的图书奖。